「道家經典研讀會」
謹訂於2006年5月27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5時,
假臺灣大學哲學系館二樓研討室201,
舉辦第六次研讀會,
會中將邀請台灣大學中文系鄭吉雄教授講演,
題目為「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
誠摯邀請您蒞臨指導。
耑肅敬請
道安
道家經典研讀會 敬邀
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
鄭吉雄[1]
2006/3/16
1. 前言
數字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發展,可以從多個不同面向切入探討。出土文獻中的「數字卦」顯示數字觀念很早就和《易》學發生關係。就《易》學而言,象數理論中的數學,部分源自筮法,[2]部分源自節候理論,[3]部分則來自陰陽五行思想。[4]就儒學思想的發展與解釋而論。近現代研究儒家思想的學者對於儒家心性論研究頗多,但對傳統儒者數字觀念所建構的形上世界秩序,討論較少。這樣認識儒學,似未夠全面。本文討論所得,也許可以對上述兩個課題,有所補充。
本文的主旨,在於說明先秦思想家如何以數字觀念解釋萬物的生成,從而建構世界秩序。本文並將說明思想史上數字觀念問題意識的轉變,尤其宋儒的數字形上學和漢儒的數字觀念有若干傳承的關係。大致來說,先秦兩漢儒者以數字觀念建構其宇宙觀。他們觀念中的世界和宇宙,是實體的、有層次的、系統性的,可以用數字呈現出秩序與架構的。道家站在反儒的立場,則一方面運用其各種數字歸納物類,一方面也企圖推翻儒典中的數字觀念體系。自魏晉時期般若學「緣起性空」思想傳入,和玄學家重新宣揚的「無」觀念經格義的過程結合後,對儒學產生衝擊。經過漫長的回應過程,北宋儒者堅持了真理和宇宙的有形跡、能實測的「有」的部分,但同時他們又強調所認知的真理和宇宙,是無邊際的、不可把握、無法以經驗層次之事理證實的,具有不為形跡、實測所限制的性質。他們明白到先秦兩漢時期以元氣論為主軸的數字觀念,已不足以因應佛教形上思想的衝擊,於是他們接受了部分漢代《易緯》與《參同契》的數字觀念,建構《易》圖詮釋的方法之後,接下來他們必須以數字觀念表達出一套有形與無限共存的形上思想。
2. 儒典中數字觀念的興起與道家的回應
數字觀念的源起很早。張政烺和出土文獻研究者發現近世出土甲骨文獻中已有數字卦的紀錄。數字卦的成卦方法,今日已不可知;成卦之法的祕密未揭開,占卦者如何利用數字建構其世界秩序,以及解釋宇宙起源,都仍是一個謎。無論如何,「數字」既可成卦,而卜卦又是上古社會神道設教的具體反映,那麼運用「數字」來探討宇宙的奧祕,和《易經》就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可謂年代甚早。《周易》成卦之法,最早見於《繫辭傳》「大衍之數五十」一段文字紀錄。根據朱子(熹,1130-1200)的解釋,「其用四十有九」,不用的一根蓍草是象徵「太極」。這雖然沒有確切的根據,但不這麼說,也很難講出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道理。「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兩」象陰陽,「三」象三才,「四」象四季,除了朱子的解釋外,也沒有更好的說解。但究竟先民是不是真的是早就有太極、陰陽、三才、四時所共構的秩序觀念,然後才運用它們來解釋《易》占過程中被實際運用的「一」、「二」、「三」、「四」這四個數字呢?這個問題受限於文獻,是無法回答的。但最特別的還是在於「十有八變而成卦」的過程。三變成一爻,四十九根蓍草到最後倘得三奇數則為「老陽」,而餘數為「九」;得三偶數則為「老陰」,而餘數為「六」;得一奇兩偶則為「少陽」,而餘數為「七」,得一偶兩奇則為「少陰」,而餘數為「八」。這種「陽卦多陰,陰卦多陽」[5]的現象,表述的是當下為「少」標誌未來為「多」,當下為「多」則標誌未來為「少」。這是相當特殊的一種表述形式;而《易》演卦之法,遇「老」變、遇「少」則不變,故《周易》爻題凡「陽、陰」通稱「九、六」而不稱「七、八」。《易經》撰著於西周初年,作者已經以數字的運算來探討宇宙萬物變化的精微之理,可以看出數字形上學的確很早就存在於東方的文明思想中。
清儒汪中(容甫,1744-1794)〈釋三九〉一文,指出先秦時期「三」和「九」這兩個數字都是「虛數」,有時「不必限以三」、有時「不可知其為三」,有些「不其果為三」,也有些「不必限以九」,有些「不可以言九」。[6]汪中所講的「虛數」指的是這些數字僅僅表達和實質數量無關的抽象意思。汪中所講的數字的運用,部分應該視為一種修辭的技巧,[7]因為它們事實上並不虛。自先秦時期開始,儒者已不斷將這些所謂「虛」的觀念,變成實質意義。以「九」字為例,「雖九死其猶未悔」、「九折肱以成醫」的「九」當然不可能視為實質數字,但如「九州」之名,春秋中期已有;[8]戰國時期的《尚書•禹貢》之中更清清楚楚地標出了每一州的名稱。[9]此外,春秋時期的數字觀念也含有濃厚的政教訓示的意味。《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記子大叔見趙簡子云: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10]
子大叔認為五行、五味、五色、五聲都是彰發於天地的,乃循天地之性而有,而人亦秉天地之性而法則之,故與此五行五色等同生並存,不可相失。這五種事物,又係該類事物中之最美好者。如六畜、五牲、三犧,其味有千百種,而處治牲犧之事,目的在於突顯出五味(而非六味、七味)之所在。亦即說,人民對五味有認識,進而將之視為法則,使不致昏亂而失其性,必須通過治六畜、五牲、三犧之事,始可達成。[11]「五色」、「五聲」的情況亦相同。子大叔的意思,是勸趙簡子勿只著眼於「儀」(如九文、九歌、六畜、五牲等節目)之上,而應注意這些小節目背後要尊奉的天人所秉的美好本性(即五色、五聲)。可以說:五味統一了六畜、五牲、三犧之味;五色統一了九文、六采、五章之色;五聲統一了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之聲。從子大叔的話,我們更可注意其中政化教訓的意味。[12]昭公元年《左傳》亦有相類似的記載: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先秦時期這一類以數字觀念建立教化的思考,五味、五色、五聲之類表達的是正面的價值。相對上,刑罰也有五刑、[13]九刑[14]之分。五刑為「墨、劓、剕、宮、大辟」,大抵無甚爭論。「九刑」之名卻困惑了古今的學者。[15]但無論如何,春秋時期已發展出以「五」或「九」等數字觀念來突顯物類之多,或物類之中最美好的幾種,來達到政治教化的目的;而這種方法顯然得到士大夫的全盤認同。孔子和孟子就時常用「三」來分類事物,以求整齊劃一。[16]這些以「三」、「五」、「九」的觀念區分物類的思想,受到老莊的強烈質疑。《老子•道經》第十二章云: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7]
《莊子•天地》云: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18]
道家最反對人為的標準,尤其這些標準可能扼殺自然天性之處。當然,問題並不在於儒家不重視自然,而是儒家對自然的態度和觀點與道家不同。故此五色、五音、五味在儒家亦為「則天因地」之物,在老子則視之為令人目盲耳聾口爽的禍害,而原因正在於五類標準的訂定與劃一,否定了其他色、聲、味的自然存在與價值。〈天地〉篇的作者更以滑稽的文筆說之,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加諸前四者之後,湊足「五」之數。「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一語,無疑是以反諷的方式,對於以「五」化約物類的思維方式作直接的否定。老子列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五者,亦似有莊子諷喻之意;否則若老子不知不覺中亦自然擇「五類」事物加以否定,則他亦不免墮入「五」的思維方式之中了。
儒家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其世界秩序,無論是五色、五音之類,都強調一種不容懷疑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本身的限制,固然被道家以一種自然的觀點全盤推翻;但就數字觀念建構世界秩序的理論本身而言,也存在嚴重的弱點,本要是其自身的自相矛盾,如《左傳》文公七年晉卻缺言於趙宣子: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19]
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倘將「穀」一項去掉,則成了戰國中期以後極為流行的「五行」。此可見這一類數字思想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立論者既要以數字量化、整齊化的方式建構世界秩序,並強調此一立論碻不可移的絕對性,但此一類立說的游移而不確定的本質,又將其必需的絕對性破壞無遺。於是儒典之中所載的各種涉及數字的觀念,也就成為經典訓釋的爭議點。如「九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楚辭即有「九章」、「九歌」,「九」的數字觀念出現更多。其中「九歌」共有十一篇,歷來注家提出各種解釋,彼此迥異,不論那一種說法能成立,總之都反映了古代哲人執著用數字說明世界物類範疇的用心。
先秦時期數字觀念除了區分物類以外,又多以空間的描述為主。如《易經》卦爻辭已有初步的方位觀念,但至戰國晚期出現的《說卦傳》,其方位觀念更趨成熟。《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以下的一段文字,明確標示震居東方,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坤居西南,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的八卦方位,並且為八卦的喻象賦予意義,如離卦,該《傳》稱: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21]
《說卦傳》明確建立了卦的方位,講了喻象,卻沒有對於各卦喻象的屬性,作詳細的引申。「八卦」和「五行」兩觀念在先秦各有其來源,[22]但在戰國時期,「離」之「火」、「坎」之為「水」,「巽」之為「木」,「八卦」、「五行」也出現了某種偶然的關係。[23]從《說卦傳》的方位觀念再進一步,就出現籠括方位、數字、季節、五行等觀念,統整一歲之中節候轉變的規律的思想。《呂氏春秋》以「木」配春居東方、其數八、其色青。《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
又以「火」配夏居南方、其數七、其色赤。《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
又以「土」配季夏居中央、其數五、其色黃。《呂氏春秋•季夏紀第六》說: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士。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駠。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又以「金」配秋居西方、其數九、其色白,《呂氏春秋•孟秋紀第七》說: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
又以「水」配冬居北方、其數六、其色玄。《呂氏春秋•孟冬紀第十》說: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
《禮記•月令》和《逸周書•月令解》亦記載了幾乎相同的內容。[24]這樣的思想,結合數字、方位、季節、五行屬性,為數字形上學開拓了新境。漢代《易》學的「卦氣」學說,可以說也是這種發展的結果。其以六十四卦分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而得出種種卦爻值日的順序,其說更為繁複。[25]
3. 漢代數字觀念的發展及其限制
數字世界觀肇興於先秦,流行於晚周,而大盛於漢代。晚周時期的《逸周書》,各篇章包括天文、地理、人事、禮制,都蘊含了大量的數字觀念,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然而,嚴格來說,先秦的數字觀念並沒有形上學的意義,因為它們並不能說明宇宙何以發生、萬物何以存在、生命的根源為何等問題。先秦儒家對於數字觀念的論述,往往僅只給予一個簡單的、量化的圖象,是直述式的,以強調它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論述。這些數字觀念被提出時,提出者甚至沒有一些起碼的描述或解釋。不過從一個比較的角度看,五行思想在東西方思想史上也並不孤獨。西方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紀,已經有了對於宇宙原始物質或元素的各種提法,和中國的「五行」相似。不過像Thales(625B.C.-545 B.C.?)提出「水」是宇宙的原始物質;Heraclitis(535B.C.-465 B.C.?)認為是「火」。Anaximenes 認為是「氣」(air);古印度以「水火土」為人的「三元素」、或以「地」、「水」、「火」、「風」為「四大」等。不過,中國的五行思想廣為先秦各思想流派所接受,既具有嚴整的系統性,也產生了漫長而深遠的影響。
漢代思想中的數字觀念,隨著陰陽五行化的儒學的傳播,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即列載各種數字觀念,該書〈官制象天〉全篇歷述三、四、九、十二、二十七、八十一、百二十等數字觀念: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其以三為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為制,取諸天之時。[26]
除了「三」、「四」兩個數字為「天經」、「天時」之數外,《繁露》接著又申論「十」與「十二」: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合於天。……求天之數,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27]
董仲舒意在說明人事與天道之間的絕對關係,而人事的分類,與身體的結構、天運的度數,都有一致的關係。他的思想多著重講天人之間關係的現象,強調這些現象的絕對性。過去馮友蘭批評董仲舒,認為他的天人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擬人觀的理論」,[28]但事實上,先秦思想史原本就存在一種以「人」為中心點而開展出來的宇宙秩序觀,董仲舒不過是特別針對數字形上觀念加以發揮而已。
董仲舒的數字觀念和先秦時期的數字觀念一樣,都著意於建立一個既符合自然現象、又具有倫理意味的世界秩序,希望政治教化能藉著數字觀念來普施萬方。這種傾向,讓他們的數字觀念系統,在理論上受到兩方面的限制:第一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預設了一個「存有」的世界。他們不曾意識到在這個「存有」世界之上,有任何含有絕對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或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層次或境界,因此也從不考慮他們運用數字所建構的世界秩序,有任何在理論上可能不夠周延之處。也許有人認為,先秦道家提出的「無」,即可以消解數字觀念所建構的世界秩序。但我認為,《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觀念,也許曾對先秦至秦漢儒者的數字觀念產生過衝擊,但《老子》的「無」觀念其實也近似於實有,這主要是因為《老子》運用了正面描述方式和語言來講述「無」。
先秦下迄西漢董仲舒的儒家數字觀念系統的第二個限制是,它們只說明數字觀念的現象,但沒有講到這種現象的原因為何,這使得他們的數字觀念的形上學內涵不夠成熟。倘若只講現象,那就表示作者可以自圓其說,當「一」和「元」不同時,他們可以說「變一為元」;當有需要包括金木水火土之實、卻要避免用「五行」之名時,可以加一「穀」而成「六府」;甚至當有需要牽合兩個不同的觀念時,他們可以利用「聲訓」的方法硬將兩者拉在一起。換言之,他們建立的數字觀念是封閉的,大部分是自己證明自己,細究其各部分,卻可能彼此矛盾。
與董仲舒同時期的司馬遷受到廣泛的數字觀念的思潮影響,尤其是董仲舒的影響。他的《史記》設立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都無不是神祕數字觀念。[29]至於道教文獻如《淮南子》、《參同契》,亦充滿著數字的觀念。
西漢初年數字觀念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前述先秦時期數字「九」並不是具體的「九」之數,而是形容事物之多。這可能和《易經》的爻題以「九」示「陽」而主「變」有關。[30]漢代的《易緯》「九者,氣變之究也」(詳下)部分說明了這個原理。因此,我們讀楚辭其中《九歌》共十一首而非九首,學者提出各種解釋。其實汪中「九者虛數」一語,已經說明得很清楚。西漢初的辭賦家原本上承楚辭的傳統。辭賦家除了用「九」來標示篇名(如王襃〈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外,又轉而運用數字「七」,於是有東方朔〈七諫〉、枚乘〈七發〉。綜觀兩漢作品,尚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至於魏晉則有曹植〈七啟〉、張協(景陽,?-307)〈七命〉。《昭明文選》就將「七」和「詩」、「賦」、「序」、「啟」等三十餘種文體並列。在中國文學史,這種文體只存活了一個很短的時期。[31]
4. 從空間到時間:數字形上學建構的初步
下迄漢代,《易》家仍然用數字觀念描述空間,並有新的創造。如《易緯•乾鑿度》「易變而為一」句鄭《注》云:
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32]
又稱: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
鄭玄《注》:
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四也。[33]
一居北方,三居東方,二居南方,四居西方。一二三四作為《易》家尊稱的「生數」,已有方位上的分佈。《乾鑿度》卷上「濁重下為地」鄭玄《注》:
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34]
坤為老陰,於數為六;坎為少陽,於數為七;離為少陰,於數為八;乾為老陽,於數為九。六、七、八、九的方位與一、二、三、四相同,因為前者為「成數」,後者為「生數」,「成數」即係「生數」加「土數」「五」(「五」居中,故屬土)而成。其實數字方位的思想,晚周時期已經大行,並且成為思想界的通義。《呂氏春秋》提出而沒有解釋;鄭玄則進一步解說: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為天一匹也,天七為地二耦也,地八為天三匹也,天九為地四耦也;地十為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五而成,故云五歲而陳將復封。[35]
依此規律,則「一」為北方之數,「二」為南方之數,「三」為東方之數,「四」為西方之數,各依其陰陽奇偶,與六、七、八、九之數耦合對應。《易緯•乾鑿度》卷上「皆合於十五」鄭玄《注》:
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大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為名焉。[36]
「太一」居北方象「水」,明顯地是先秦五行說的舊義,《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篇即反映此一觀念。[37]但數字分居四方,而有生數、成數之分,甚至以仁義禮智信、心肝脾肺腎分配五方,都是出自漢儒的創造。[38]更重要的是,數字方位的觀念,成為宋代《易》圖之學最重要的元素。劉牧(長民,?-?)《易數鉤隱圖》的數字方位,就是奠基於《乾鑿度》和鄭康成的理論。(說詳後。)《乾鑿度》說:
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
鄭玄《注》云:
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39]
鄭玄的解釋,只提到太一周行九宮的次序,並沒有提到方位;但朱伯崑據此,繪成「九宮圖」(圖A)。[40]其中「太一」居中宮,數為五。其餘八卦方位分佈,則依《說卦傳》之說。不過朱說當然也有依據,因為《乾鑿度》本身即承襲《說卦傳》的卦位說;鄭玄注《乾鑿度》,照道理不會違悖。
無論如何,鄭玄的解釋,描述了一個宇宙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以「太一」為主體,進行八卦九宮的周遊,可以說是數字觀念的一種新發展。回溯數字觀念的發展過程,思想家最初以數字觀念描述空間,漸漸發展到描述時間,尤其用以描述宇宙的發生的過程。《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三統曆》: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41]
《易緯•乾鑿度》:
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
鄭玄《注》:
「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為一,謂變為「太初」也;一變而為七,謂變為「太始」也;七變而為九,謂變為「太素」也。「乃復變為一」,「一變」,誤耳,當為二。二變而為六,六變而為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者,謂足相推明耳。[42]
這是以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分析太易衍生變化的數字理論。鄭康成對於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發揮,是用「無」來解釋「太易」。先秦以迄漢初的宇宙論,對於宇宙的源起與生成,多用正面的方式描述。即使思想家強調「無」,也將「無」視為一種類似實體的事物。[43]前述《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即如此。又如《淮南子•天文》說:
天地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太始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清陽之合專易,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44]
既云「未形」,卻可以正面描述;既可以正面描述,就很難成為徹徹底底的「無」。唯至《易緯•乾鑿度》卷上「故易始於一」,鄭玄《注》說:
易本无體,氣變而為一,故氣從下生。[45]
「易无形畔」鄭玄《注》說:
此明太易无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曰:「易无體」,此之謂也。[46]
對於「太易」,鄭玄如此解釋:
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為太易。[47]
「易變而為一」句下鄭玄說:
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
「一變而為七」句下鄭玄說:
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
「七變而為九」句下鄭玄說:
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
「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句下鄭《注》說:
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48]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鄭《注》說:
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
康成所說的「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就是說「太易」是超越於人類感官認知的層次的「無」的狀態。這樣的描述,和《淮南子》對「太昭」的描述相比較,更貼近一個絕對而超越經驗界的「無」。「有理未形」四字,也更貼切地講出一個超越於形質世界的「理」。當然這句話太簡單。「理」的本質是什麼?是不是一個絕對抽象而普遍的本源,抑或只是沒有形體的實質存有,其實還是不清楚的。然而,從「太易」演變到「太初」,可以確定是從「無」演生為「一」(氣漸生之始,鄭玄形容為「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從「太初」演變到「太始」(陽氣壯盛、自北方始、居坎位、天象形見之所本始),是由「一」演生為「七」;從「太始」演變到「太素」(陽氣終究於西方、居兌位、地質之所本始),是由「七」演生為「九」。這樣的解釋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太易」近乎「零」的觀念。如前所說,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一大特點,是預設一個存有的世界,亦即形質的世界。如果借用理學家理無形跡,氣有形跡的講法,數字觀念有效地說明了宇宙和世界氣化流行的過程和原理,但對於「無形跡」之「理」,卻無法加以說明。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思想只有一、二、三、四以迄千百萬,卻一直沒有「零」的觀念。而今鄭玄提出「有理未形」、「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已經隱約指出了一個超越於形質,甚至超越於「氣」的絕對的「無」。他顯然接受了《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但他對此四字,顯亦有其新詮;而其新詮,對於宋儒是很有啟發的。
第二、數字觀念不再只是處理「空間」(亦即方位)的問題,也處理了「時間」的問題,亦即宇宙萬物生命原始的過程。從「虛豁寂寞」的「太易」,到一、七、九。[49]
5. 邵雍、劉牧《易》圖數字觀念對漢《易》的承繼與發揮
前文述及鄭玄利用《乾鑿度》一、七、九的數字觀念,結合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者,論述了一個自「無」而「有」、以「氣」論為基礎的宇宙生成過程。如前所說,數字觀念預設一個存有的世界,說明宇宙氣化流行的過程和原理,但對於「無形跡」之「理」,有著先天上無法加以表述的弱點。這是數字觀念本身的限制。
自印度佛學傳入中國,般若學者運用「遮詮」(negation)的方法,顯示「空」義,給予中國思想界相當大的衝擊。如我們所知,漢末何晏(平叔,190-249)倡「貴無論」,裴頠(逸民,267-300)撰《崇有論》,有無之辨歷經魏晉一段長時期的討論,已十分透徹。何晏與王弼(輔嗣,226-249)所講的「無」,是透過概念的分析,推理而得,與《淮南子》所繼承的稷下黃老視「無」為實體存在的思想,已為一大進步。[50]然而,「有無之辨」的辯論焦點,是宇宙萬物根源的問題,崇有論者認為存有本身即係本源,一切行為價值衡定的準則均在存有界之中;貴無論者認為存有的世界所依恃的是本體之「無」,因此應以「無」作為一切行為價值衡定的準則。換言之,持「貴無」思想的學者提出「崇本舉末」、「聖人體無」之論,其實亦未嘗將存有的世界全部否定。
佛教思想則不然,空性觀念的輸入,不但將存有界的一切事物視為變滅無常的全體虛幻,甚至於「空」自身亦不可執恃。《中論》「觀因緣品」以「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八不」說明「中道」之義。換言之,中道是一種雙遣的方法,透過對相反之兩端的同時否定,來呈現「中」的境界。如果先秦以降道家思想對於「無」多用正面的描述可稱為「表詮」,那麼般若學的「空」就是一種徹底的透過否定來呈現的「遮詮」。從思想史的過程觀察,佛教思想的「空」觀念對於儒家思想的挑戰,比起道家思想的「無」觀念來說,可能要大得多。
在漫長的回應過程中,儒家學者沒有放棄其固守了千百年的、以存有論為主的思想立場,但對於釋老思想,尤其是佛教的「空」的思想,又必須予以回應。儒學發展至北宋,理學肇興,道學家採取了不同於數百年前裴逸民「崇有論」的路徑,充分汲取佛教思想的資源,對於儒典重新予以解釋。他們一方面承認存有世界包括禮儀、政教、踐履道德等一切意義,一方面又充分汲取釋老「空」、「無」之義,在建構其形上學時,時常強調宇宙的根源的「太極」、「理」、「太和」等觀念,具有不落於形氣、不規限於實跡的特質。
北宋道學家的立論取向中,有兩個特點值得吾人注意:第一、他們多將其理論依據建築在《周易》一書之上──如周敦頤(濂溪,1017-1073)撰《太極圖》、邵雍(康節,1011-1077)立先天之學、張載(橫渠,1020-1077)著《正蒙》、程頤(伊川,1033-1107)撰《易傳》。北宋理學家幾無不如是。可以說,若不能了解《周易》一書,對宋代理學的了解也就很有限。第二、他們治《易》發展了「圖書」一門,與《易》哲學史上「義理」、「象數」二派鼎足而三。
宋代《易》家雖然有新創,但我們也切不可因為漢宋異同,就誤會宋《易》和漢《易》無關。事實上,宋《易》有許多來自漢《易》的觀念。如前述《乾鑿度》之「九宮圖」,與宋代劉長民《易數鉤隱圖》的「河圖」,邵雍、朱子的「洛書」是一樣的,即為一證。(說詳下。)在這裡我再舉最擅長於運用數字描述時間的邵雍為例。《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年」五單位描繪了宇宙時間的圖譜:一世為三十年,十二世得一運,則一運為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則一會為一萬零八百年;十二會為一元,則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邵雍的數字區分法,針對的是時間而不是空間,而他的理論,也是源出於漢儒的思想。首先,三十年為一世,就是漢儒的講法。按《論語•子路》: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穎達《疏》說:
三十年曰世。[51]
《說文解字》「世」字在「卅」字之後,許慎說:
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皆从卅。世,三十年為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52]
「三十」為一「世」的講法,除了許慎宣稱的字形字音的近同以外,又《史記•天官書》說: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53]
一世三十年亦出於漢儒無疑。至於「十二世得一運」,於古無徵,但《左傳》已「十二會」、「十二辰」的講法。《春秋》昭公七年《左傳》記晉侯問伯瑕「何謂辰」,伯瑕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預《注》: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54]
杜預解釋的「十二會」或「十二辰」是指「一歲」,與邵雍「十二會」指「一元」的講法不同。但「所會謂之辰」,則「會」與「辰」同義。如與《漢書•律曆志》參看,合理的推測,則「十二會」應該是從「十二辰」之說變異而來。「十二會」為「一元」之說中,「元」作為最大的觀念,它的意義來源就顯得更為重要。《漢書•董仲舒傳》: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55]
《春秋繁露•玉英》: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56]
「元,猶原也」是一種聲訓的策略,亦即用主觀地用「元」的同音字「原」來演繹「元」的意義,將它的意義規範在「溯源」、「原本」之義上。「元,猶原也」就是說「元」是宇宙的本源。《易緯•乾鑿度》有「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的卦爻紀年月日的方法。其單位由小至大,依次分別為「日」、[57]「月」、[58]、「歲」、[59]、「大周」、[60]、「紀」、[61]、「世軌」、[62]「部首」、[63]、「元」。[64]其中「元」是最大的單位。《乾鑿度》又說:
易一元以為元紀。
鄭《注》:
天地之元,萬物所紀。[65]
《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
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66]
孔《疏》:
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67]
又《漢書•律曆志》說: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68]
邵雍固然不是元氣論者,但他尊「元」的態度實受到漢儒以降儒典詮釋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69]再擴大一點看,邵雍以由小至大、循序漸進的單位描述宇宙時程,最大的「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與漢儒思想亦近似。如《乾鑿度》稱:
以七十六乘之,得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70]
這種由小至大,推衍至於千萬年的思想,《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亦有提及: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
孟康《注》:
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71]
「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指「一」為開始,一、三、五、七、九相加,得二十五。「八十一章」是以九九究極之數自乘。八十一乘以十九,得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漢書•律曆志》又引劉歆《三統曆》說: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72]
《乾鑿度》以日、月、歲、周、紀、世軌、部首、元等推衍,可得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年。劉歆《三統曆》「十二辰」自「始動於子」,至「參之於亥」,以「三」的倍數增加十一次,推衍可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皇極經世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總共四個數字相乘,推衍可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三個演算的過程不同,得出的數字亦相異,但其實所運用的模式,卻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從「卦氣說」的理論模式轉變而成。就邵雍的系統而言,「十二」和「三十」也是《史記》的神祕數字。十二為地支之數、一年之月數,《春秋》十二公的數目,也是消息卦的總數;「三十歲一小變」之說,是否與「世」的形音有關,已不可實證;不過「三十」與「十二」均為漢代的神祕數字,是毫無疑問的。
總之,從上文分析來看,數字觀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關係極密切。近年學術界如黃沛榮師早已指出曆法中之數字,如十、十二、三十、三百六十等常被用作「天道」之代表,以與人事相應。[73]
6. 宋儒數字觀念中的「數」與理氣問題
宋儒持數字觀念者甚多,本節集中討論理氣問題,而舉兩人為例。一為邵雍《觀物篇》,其理論以「理」為主體,而傾向於「象」學;一為劉牧《易數鉤隱圖》,其理論以「氣」為主體,而傾向於「數」學。[74]以下先論劉牧。
北宋《易》家鮮少純用「數」論《易》,唯有劉牧《易數鉤隱圖》異於眾論。這是因為劉牧認為「數」是才是一切形象的根本。《易數鉤隱圖•序》說:
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75]
劉牧所講的「形」,指一切具體的、有形之物;「象」指剛柔、往來的抽象之事;「數」即指數字。這是說,「數」是根本,有數始有象,有象始有形。故劉牧不承認「五行」中的金木水火為四象的說法,他說:
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故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為象哉?孔氏失之遠矣。[76]
唯有「數」才是顯豁地指出形上世界的演化過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所謂「生數」,《易•繫辭傳》所記天地之數,即係記天地演化過程的數字紀錄。他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地六而上,謂之道也;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77]
至於「五」,即《繫辭傳》及劉牧所謂「天五」(雄按:即漢唐儒者所謂「土數」),上不在生數之中,下不屬成數之列,是使「生數」轉化成為「成數」的關鍵之數。他說:
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地十應五而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78]
由一至十相加,而得五十五,即劉牧所謂「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試看「天地之數圖」(圖B)。《易數鉤隱圖》說:
內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數也。兼五行之數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數也。[79]
雄按:「太極」為天地之之體;生數「一」、「二」、「三」、「四」及土數「五」相加,得「十五」,是「天地之用」,亦係用九用六、九六相加的結果。「五行之數四十」,即成數「六」、「七」、「八」、「九」及五行之成數「十」相加而成。「五十五」之數,是劉牧理論的代表性之所在。[80]
劉牧論「四象」,亦依「數」與「象」,加以區分。即認為有二義:
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81]
一種是「兩儀所生之四象」(或稱生八卦之四象),亦即以「數」為本的「象」:
象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象也;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82]
第二種是「所以示之四象」:
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83]
綜合起來看,劉牧的數字理論的基本概念,幾乎全部來自漢儒的舊說。然而,漢儒的舊說只提出數字的方法,或混合聲訓的方法(如「九」之為言「究」之類)提出簡單的宇宙演變。劉牧則有新的創造,就是以一至於十的數字來建立其形上學理論。首先,他以陰陽二氣交感為「太極」(請參圖C)。《易數鉤隱圖》:
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為一以畫之,蓋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84]
如前所述,數字觀念系統的限制之一,是適合講述形質的世,而不適合講述超越形質層次的理念,主要因為中國數字觀念沒有運用「零」。劉牧亦不例外地受到這種限制的規範。因此,依劉牧所論,「太極無數與象」,那「太極」就不是「一」,不是「一」那應該就是「零」;但既然劉牧又「以二儀之氣混而為一以畫之」,既可以混而為一以畫,則又不應該是「零」。[85]事實上劉牧又說:
太極者,元炁混而為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謂。……今質以聖人之辭,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既言有,則非无之謂也。不其然乎?[86]
劉牧明確地強調,「太極」是「其炁已兆」,因此不是「无」。「太極」既不是「无」,那就必然是「一」,豈能說「無數與象」呢?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形上學的限制。而劉牧論太極生兩儀(圖D)說:
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一氣所判,是曰兩儀。……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之象也。[87]
古人觀測太陽自東而西,即所謂「天左旋」;地軸轉動自西而東,即所謂「地右動」。劉牧佈列數字,認為天一居北、天三居東、地二居南、地四居西,恰好反映了天地的「上下未交之象」。
劉牧受漢儒數字觀念的啟示,進一步以數字觀念建立形上理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太極」究竟是「理」抑或為「氣」的問題。而根據上述的分析,劉牧雖然說「太極無數與象」,但他既說「其炁已兆」,又以「二儀混而為一」來畫「太極」,那就明確地顯示劉牧所持的是一種氣化宇宙論。
簡而言之,劉牧認為「數」的成長,既反映了宇宙演化的過程,也是萬物源始化生的過程。掌握了「數」,就掌握了形上之「理」氣化流行,化生萬物的規律。這就是《易》的奧義。
《易數鉤隱圖》明確地以數字系統解釋宇宙萬物漸次生成的過程。邵雍亦重視「數」。他的《皇極經世書》的「數」的理論,已略述於前文,茲不複述。邵雍雖然亦以數字佈列宇宙時程,但其思想實以「理」為本,而非以「數」為本。《觀物外篇》說: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88]
又說: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89]
「理」是最重要的,而觀察「理」的則是「心」,因此「心」是第二重要的。邵雍說: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90]
和北宋的道學家濂溪、橫渠一樣,邵雍很看重「心」,也看重「中」。《觀物外篇》說: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91]
尚「中」的思想,其實早在先秦即已是思想界的通義。從尚「中」思想,以及《易》往復循環的道理,又啟發了邵雍在卦爻的關係中探討天地終極的原始點:
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自姤至坤,為陰含陽;自復至乾,為陽分陰。坤、復之間為無極,自坤反姤為無極之前。[92]
「坤復之間」,即為「一陽初動」的變化。邵雍很重視這個稱為「無極」的時間點。「無極」一詞,道教的意味很濃厚。然而,我不認為邵雍真的主張「無」是宇宙根源。所謂「坤復之間」者,其實指的就是陽氣始生的一剎那,所以「無極」也就是強調這一剎那的神祕性。事實上也就是陰陽交轉活動過程的一個重要時間點。他有詩說: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93]
他認為「天心」正在於冬至一陽初動之處。所謂「初動」,就是將要動卻又尚未動的意思,所以說是「萬物未生時」也。這就是邵雍「天根」、「月窟」之論。他有詩句說:
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94]
「乾遇巽」,就是乾卦變為巽卦、一陰初動之時;「地逢雷」即坤卦變為震卦、一陽初動之時。前者為「月窟」,「月」是太陰之精;後者為「天根」,「天」指「日」,「日」是太陽之精。因此黃宗羲《易學象數論》說:
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為天根,以其為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為月窟,以其為一陰所生之處也。[95]
黃百家說:
邵子之說以得半為「中」,又不敢至於已半,而以將半為「中」也。[96]
邵雍的數字觀念,和劉牧一樣,雖然多來自漢儒的舊說,但他也有新創,就是超越了「數」的限制,直指「數」背後的「理」。可以說,邵雍所持的,是以「理」為體,以「數」為用的數字形上理論,而「天根」、「月窟」兩個觀念,則是宇宙萬物初生初動的起始點。作為形上學理論,將這個根源及其演生的原理作出系統性的描述,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必須同時掌握《觀物篇》的宇宙時程、先天諸圖的理論架構,以及邵雍尚「中」的天根、月窟觀念,才能窺邵雍思想的全貌。
7. 結論
從先秦時期數字觀念思想的發生歷史考察,我們注意到數字觀念出現很早,而且非單一來源。《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頭,稍晚至於春秋時期,《左傳》、《詩經》、《尚書》等儒典所記,數字觀念已經大行。戰國晚期數字觀念延伸至於四季、五方、顏色等各種自然界事物,形成了繁複而獨特的宇宙秩序。西漢時期數字觀念繼續朝向神祕化、複雜化的方向發展,以卦氣觀念為核心的思想影響所及,幾無處不在。《春秋繁露》、《史記》、《白虎通義》、《易緯》等幾種文獻的數字思想以及鄭玄的經注都反映了此一情況。儒學經過魏晉有無之辨的洗禮,又受到佛教思想的衝擊。般若學「空性」的思想在理論上徹底摧毀了存有世界的一切意義。儒家思想在回應佛教思想的漫長過程裡,逐漸感到舊有數字觀念只注意存有層面的限制。於是宋明儒者努力地試著一方面運用數字描述形質世界的秩序和意義,一方面又想盡辦法,超越數字的限制,處處強調數字所表述的形上本體的普遍性和超越性。這種試圖兩面兼顧的努力,在劉牧、邵雍的《易》圖詮釋中表露無遺。然而,以數字表達抽象觀念,有一定的限制。它較易於表達「有」的層次,較難觸及「無」的層次。儒家原相信一個存有的、有秩序也有意義(意義即來自於秩序)的世界,數字觀念適切地替這樣的思路服務。
另方面,過去講思想史的學者,常常區分漢宋。其實從漢到宋是一個過程,整個思想史也是一個過程。沒有漢代哲學對數字觀念的建構,宋代理學家也無法建構其數字觀念的世界;沒有佛教思想的刺激,儒者也不會那麼認真地思考數字觀念的限制。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倘能明瞭於此,也許就不會過度在漢代思想與宋代思想之間,作出貶抑與褒揚了。
附圖
圖A 圖B


圖C 圖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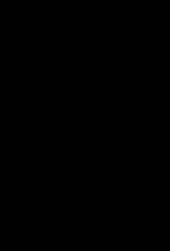

[1]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2] 如《繫辭傳》所記「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節的成卦之法。
[3] 包括二分二至、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及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等。
[4] 主要是五行思想及其相關的數字方位問題,如以一、二、三、四分居北南東西,成數五居中央之類。
[5] 《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雄按:本文所引《五經》內容,皆用藝文印書館之「十三經注疏」本,故下引出版資料均省略。),頁168下。
[6] 汪中《述學》〈釋三九〉說:「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原註: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收入《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頁73-74。
[7] 如《詩經•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云:「九罭,繌罟小魚之網也。」《孔疏》云:「釋器云:『繌罟謂之九罭。……』郭朴云:『繌,今之百囊網也。』……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繌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毛詩注疏》,頁302下。)又《詩經•豳風》〈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云:「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孔疏》云:「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同前引書,頁296下、297上。)
[8] 如撰著於春秋魯僖公年間的《詩經•商頌》〈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鄭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毛詩注疏》,頁794上。)又《春秋》襄公四年《左傳》記魏絳云:「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左傳注疏》,頁507下、508上。)
[9] 依次分別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10] 《左傳注疏》,頁888-890。
[11] 沈玉成《左傳譯文》譯此段文字為「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犧,以使五味有所遵循」,意義含混,似未把握到這段文字的意思。(《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87)
[12] 前引《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文字,緊接著下文為:「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行禍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左傳注疏》,頁891。)可見上述自然物類的分類,所謂九文、六采、五章之類,與倫理事物如君臣夫婦之類,個人心性之物如好惡、喜怒之類,都是一體相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協天地之性」,使政教能長久。這是本文歸結這段內容於「政化教訓」的意思。
[13] 《尚書•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尚書注疏》,頁40下。)又:「汝作士,五刑有服。」(頁44下、45上。)
[14] 《左傳•文十八年》:「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左傳注疏》,頁352上。)
[15] 賈逵、服虔說之為「正刑一、議刑八」(《左傳注疏,頁352下。)《漢書•刑法志》韋昭《注》釋九刑為五刑加以流、贖、鞭、扑四刑。(參《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95。)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古代的刑法恐不止九種,而一旦我們發現有第十種存在,前說便不得不重加檢討。而且《刑法志》和鄭玄的時代尚晚於賈、服,並皆距古已遠,賈、服既非,鄭、班未必便是。
[16] 如《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等,即曾子也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云云,《論語》的編者也有「南容三復白圭」(先進)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也有「所就三,所去三」(告子下)、「君子有三樂」(盡心上)。
[17]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4年初版,1996年第4刷),頁45、46。
[18]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61年初版,1997年第8刷)第二冊,頁453。
[19] 《左傳注疏》,頁319上。
[20] 《論語•子罕》云:「子欲居九夷。」馬融:「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疏〉:「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論語注疏》,頁79下。)依照邢昺的講法,「九夷」本身已有二義。「九夷」以外,又有「四夷」之名。《莊子•天下》說:「通四夷九州。」一般人所熟知的「四夷」為「夷蠻戎狄」的總稱,「夷」則為東方外族的名稱,故又與蠻戎狄並列。然而《周禮•職方氏》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周禮注疏》,頁498上。)鄭眾以「四夷」為專屬東方的「夷」的數目之名。鄭玄亦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亦以四夷為專指東方的夷族。惟賈公彥〈疏〉云:「先鄭(雄按:謂鄭眾)云『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以為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為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也。」(同前引書,頁498上。)雄按:賈氏以「四夷」為「夷蠻戎狄」的總稱。然而夷蠻戎狄為四方外族的專名,此處於一一列舉蠻、戎、狄之際,忽然用上「夷」的通名一義,是十分奇怪的。顯然賈氏狃於「九夷」的觀念無法擺脫,故認為「夷之數皆言九」;不知即「九夷」本身就有不同的義解。再者,說者儘可舉出九夷的名目,其至說法可以各各不同,卻不能說東方夷族非有九類不可。所謂九夷為畎夷于夷云云,不過擷其大者九種以代表全數,並強調其數之多而已。故《尚書•旅獒》云:「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偽《孔傳》云:「九、八,言非一。」(《尚書注疏》,頁183。)可見九夷強調的是眾多的夷,而非有確定的九夷之數。
[21] 《周易正義》,頁184上。
[22] 前者自西周初年卦爻辭編成即已有;後者參《左傳》「六府三事」之說,可以定為春秋時期,但與《易經》的思想系統無關。
[23] 我之所以用「偶然」二字是有理由的。「兌」與「金」同居西方,但《說卦傳》記八卦中「乾為金」,則「兌」與「金」並沒有關聯。(漢儒認為「兌」、「肺」、「金」、「義」俱居西方,是後起的思想。)
[24] 文繁不錄。讀者可參原書。
[25] 卦氣值日說,基本上是以四正卦分值二至二分,而以剩餘的六十卦分值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至於如何以六十卦分值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則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孔穎達(574-648)《周易正義》引《易緯》六十卦三百六十爻、每卦主六日七分之說,方法是以六十卦除三百六十日,每卦得六日;其餘五又四分之一日,每日分為八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除之,每卦得七分。第二種是《新唐書》一行《卦議》所記京房的分配法。方法是以頤、晉、井、大畜四個在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前的卦為各值五日十四分,坎、離、震、兌四正卦為各值七十三分。(此亦為「六日七分」說。如春分以前為「頤」當值,則「頤」之五日十四分與春分「震」之七十三分相加,為六日七分。餘此類推。換言之,四正卦本身亦須值日,而當值之時間,即從前一卦之時間分割而來。)小計得二十四日二十八分。其餘五十六卦各值六日七分。小計得三百四十日又七十二分。合計共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第三種方法載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易軌》,以四正卦二十四爻各主一節氣,而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又四分之一日「以通閏餘」。(以上可參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84-85。)
[26]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2年初版,1996年2刷),頁216。
[27] 同前註,頁217-218。
[2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1995年3刷)第3冊,頁67。
[29] 十表應十天干,十二本紀應十二地支,八書應八卦,三十世家應「世」字本義,七十列傳即以五行分配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得七十二。故《史記》記各種物類數目,多七十或七十二。說詳黃沛榮師〈史記神祕數字探微〉,刊《孔孟月刊》21:3(民國71年),頁41-46。
[30] 過去《易》學者或以為爻題晚出,但《上博簡》《周易》殘簡刊佈後,證明戰國時期已有如今本的爻題。濮茅左稱:「楚竹書《周易》爻位,有陰陽,以六表示陰爻,以九表示陽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為序。……陰陽爻位的稱法,自竹書至今本,一脈相承。楚竹書《周易》證明了『九六』之稱,在先秦確已存在。」(參《戰國楚竹書》第三冊,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年,頁134。)
[31] 蕭統《昭明文選》卷三十四、三十五收錄以「七」為題的作品共三篇。
[32] 《易緯•乾鑿度》,頁11。
[33] 同前註,頁13。
[34] 同前註,頁30。
[35] 春秋昭公九年《左傳》《正義》引鄭玄,《左傳注疏》,頁780上。
[36] 《易緯乾坤鑿度》,頁32。
[37] 關於〈太一生水〉與《易》理之間的關係,詳參拙著:〈從《易》占論儒道思想的起源──兼論易乾坤陰陽字義〉,日文版即將刊登於《中國哲學》34(北海道:中國哲學會,2006年)。
[38] 以仁義禮智信配五方,漢儒的說法亦不一。《乾鑿度》記孔子曰「東方為仁」、「南方為禮」、「西方為義」、「北方為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易緯•乾鑿度》,臺北:成文出版社,「無求備齋易經集成」本,1976年,第157冊,頁9)。但《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即指水居北方,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土居中央。《春秋繁露義證》,頁321。)同書〈五行相生〉:「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以上《春秋繁露義證》,頁362-365)。以「信」居中央,以「禮」居北方,以「智」居南方,與《乾鑿度》不同。《白虎通義•性情》稱「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肺者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腎所以智者何?腎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4年,上冊,頁383-385。)以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屬土而言,則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均與《乾鑿度》相同,與《繁露》不盡同;北方為智,中央為信,則與《乾鑿度》相反。
[39] 《易緯•乾鑿度》,頁32。
[40]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頁172。
[41] 《漢書》,頁961。
[42] 《易緯•乾鑿度》,頁30。
[43] 此在先秦時期,《老子》即頗有將「無」描述成實體的痕跡。《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44] 「太始生虛霩」原作「道始於虛霩」,此據王念孫考證而改。《讀書雜志》「淮南內篇第三」「太昭、道始於虛霩」條指出「太昭」當作「太始」,形近而誤。《雜志》又說:「『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霩』為『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讀書雜志》(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82。雄按:王說是。馮友蘭說:「道從『虛霩』這種狀態開始(『道始于虛霩』)。由『虛霩』生出『宇宙』。這以後才有元氣。這是一種『有生于無』的思想的發揮。」(氏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十九章第三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三冊,頁141。)馮友蘭似未見《讀書雜志》的考證,以致不知「道生于虛霩」為「太始生虛霩」之誤;但這一段文字確如馮氏所說,是「有生於無」思想的發揮。不過《淮南子》所講述的「太始」、「虛霩」等「無」觀念,是一個實體的「無」,並非抽象概念的「無」。
[45] 《易緯•乾鑿度》,頁18。
[46] 同前註,頁10。
[47] 同前註。
[48] 同前註,頁10-11。
[49] 或說康成不過發揮《乾鑿度》的思想,實則不然。《乾鑿度》稱:「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這段話是依易卦六爻自下而上而言的。康成注「易始於一」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為一,故氣從下生也。」
[50] 《列子.天瑞》《注》記平叔〈道論〉說:「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色形神而彰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11。)平叔的意思是:「有」是有限制的,而「無」是沒有限制的。居於「有」層次的事物,方者不能圓,圓者不能方;黑者不能白,白者不能黑。倘若宇宙本體為「有」,則世界萬物必不能方圓並存,黑白互見;唯世間萬物,黑者極黑,白者極白;方者極方,圓者極圖。這恰好證明宇宙有一「與物無對」的本體,作為其源頭。這個體就是「無」。假設沒有了「無」,相反的事物就不可能在世上並存了。王輔嗣以「無」說《易》,亦係依此一原理。換言之,雖然何、王二人理論立足於「有生於無」一語,但他們以現實界的相反並存的現象,逆推宇宙本體為「無」,較諸晚周漢初稷下黃老思想,相去已不啻千里。
[51] 《論語注疏》,頁117上。
[52] 《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頁89。
[53]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344。
[54] 《左傳注疏》,頁766。
[55] 《漢書》,頁2503。
[56] 《春秋繁露義證》,頁68-69。
[57] 《乾鑿度》有「一歲積日法」,每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即約29.531日。
[58] 參前註「一歲積日法」:每歲的月數為「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即約12.368日。
[59] 「歲」即「年」。
[60] 雄按:兩卦(計十二爻)當一歲,《易》六十四卦周一遍即三十二歲為一「大周」。
[61] 《乾鑿度》:「七十六為一紀。」則每紀七十六歲。
[62] 《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為世軌。」雄按:即以十天干各一紀計算,一世軌為760歲。
[63] 《乾鑿度》:「二十紀為一部首。」則一部首有1,520年。
[64]《乾鑿度》鄭玄《注》:「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則一「元」4,560年為最大之單位。頁39。
[65] 《易緯•乾鑿度》,頁4。
[66] 《公羊傳注疏》,頁8。
[67] 同前註。
[68] 《漢書》,頁964。
[69] 「元」字原為《易經》「乾」卦卦辭首字,歷代儒者深受此一觀念影響。如朱熹亦極重視「元」。〈仁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70] 《乾鑿度》,頁39。
[71] 《漢書》,頁963。
[72] 《漢書》,頁964。
[73] 詳黃沛榮師:《周書周月篇著成的時代及有關三正問題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37種,1972年)。又詳〈史記中的神祕數字〉一文。
[74] 宋《易》象數理論為一大宗,即使「圖書」一派,其理論基礎,亦多承襲漢儒象數。當代有些《易》學史認為古今《易》主流為義理與象數二派,有些學者主張分為義理、象數、圖書三派,其故在此。象數之中,有傾向「數」學者,或被稱為數學派;有傾向於「象」學者,或被稱為象學派。朱伯崑先生《易學哲學史》即用此一標準區分。然而,朱先生大著將邵雍歸為「數學派」,而只認為劉牧「推崇河圖洛書」:「(宋易)象數學派的倡導者,始于北宋初的華山道士陳摶,陳摶又傳其易學至劉牧和李之才。劉牧推崇河圖洛書,李之才則宣揚卦變說。以後周敦頤著重講象,提出太極圖說;邵雍則著重講數,提出先天學,被稱為數學派。」參氏著《易學哲學史》第二卷,頁6-7。這是大可商榷的。我的看法認為,劉牧才是真正的數學派。
[75] 劉牧:《易數鉤隱圖》(《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143冊),頁1。
[76] 《易數鉤隱圖》,頁16。
[77] 《易數鉤隱圖》,頁72。
[78] 《易數鉤隱圖》,頁72-73。
[79] 《易數鉤隱圖》,頁25。
[80] 朱震《漢上易傳》:「范諤昌傳劉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雷思齊《易圖通變》:「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不鮮。至劉牧乃增至五十五,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倡述。」
[81] 《易數鉤隱圖》,頁17-18。
[82] 《易數鉤隱圖》,頁17-18。
[83] 《易數鉤隱圖》,頁18。
[84] 《易數鉤隱圖》,頁5。
[85] 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中說:「聖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於是乎布畫而成卦,營策以重爻。」(頁105)「无中得象」,又顯示他頗有貴「無」的傾向。
[86] 《易數鉤隱圖》,頁32。
[87] 《易數鉤隱圖》,頁7。
[88] 為方便起見,本文引用邵雍著作,均轉引自《宋元學案》。參《宋元學案》卷九(《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三冊),頁453。
[89] 《宋元學案》,頁447。
[90] 《宋元學案》,頁472。
[91] 《宋元學案》,頁451。
[92] 《宋元學案》,頁472。
[93] 《宋元學案》,頁478。
[94] 《宋元學案》,頁485。
[95] 《宋元學案》,頁484。
[96] 《宋元學案》,頁473。